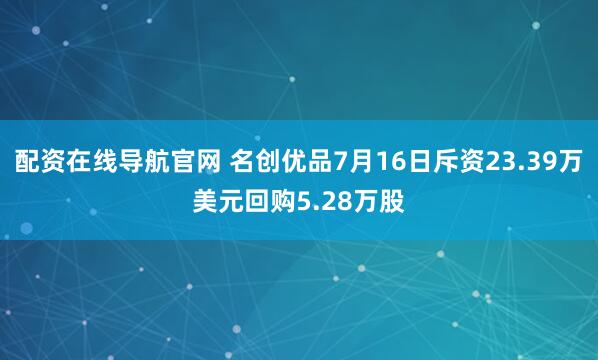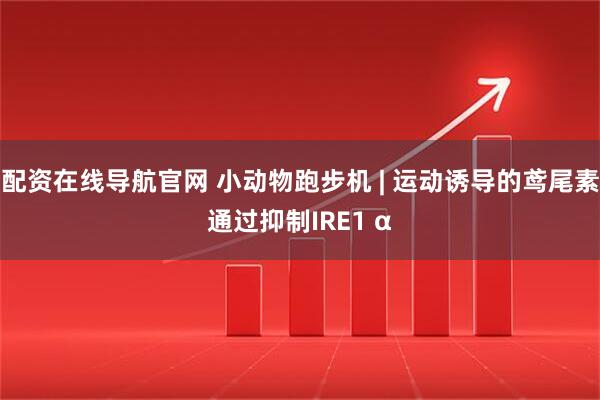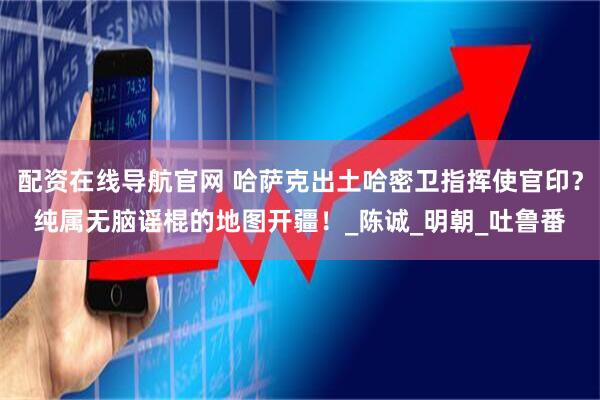
2025年4月底,有人在知乎论坛上发布神文:哈萨克斯坦出土大明哈密卫指挥使印!
由此引发大量明粉高潮,并且本能的扮演起卫道士。丝毫不顾及事实如何,沉迷于网络论战的一错再错!
首先,如此重要的历史发现,应该由国家文物局网站发布,并且入选年度全国十大考古发现!然而,从2017年至今,没有任何考古相关材料提及过哈密卫指挥使司印。
展开剩余89%国家文物局网站:http://www.ncha.gov.cn/index.html
既然官方没有认定,那就可以当作谣言看待。
对权威已经认定没有的东西,某些群体依然撒泼打滚,其常见症状如下:
1 按照刘大夏烧毁郑和下西洋图纸的逻辑,断定明朝的实际疆土和开拓成果,都被无耻的满清抹黑。满清故意抹黑明朝,掩盖大明的真实战斗力。
2 西方世界在15-16世纪出现质变式飞跃,一定是有西方人偷窃《永乐大典》。或者是有不甘心臣服满清的明朝遗民,下南洋后再将先进文明去欧洲。
3 既然死无对证,那就无法证伪。可以意淫明朝的伟大成就被西洋人窃取,并且持续性遭到西洋人抹黑。特别是故意夸大明军和欧洲海战中的拉跨表现,达成扭转认知目的。
4 不顾清朝在稳定西北边疆上的实际贡献,谎称满清在收复汉唐西域故地后,还要系统性抹杀明朝在西域领土的活动痕迹。唯有哈密指挥使司印,因在今天哈国境内才逃过一劫。
以上言论经不起推敲,逻辑主打一个无法证伪。因为掌握相关证据的人都作古,所以没人能说这个说法是假的。这种诡辩逻辑其实非常幼稚,因为没有人可以证伪,所以就可以信口开河!
事实上,明朝的哈密卫就在今天新疆哈密。永乐十二年,行在吏部验封司员外郎陈诚出使西域。他归国后撰写《西域番国志》,其中就有《哈密》章云:
哈密城居平川中,周围三四里,惟东北二门。人民数百,住矮土房。城东有溪流,水西南流。果林二三处,种楸杏而已……蒙古、回回杂处于此,衣服礼俗各有不同。
卫星地图上的当代吐鲁番 哈密与嘉峪关位置
若还有人要狡辩,硬说古代哈密不是今天的新疆哈密,无疑会被明朝士大夫的笔记打脸。我们对应陈诚笔下的具体描述,可以看他对哈密至吐鲁番区域的自然地理描写,也能很清晰的定位哈密就是今天新疆东大门的哈密:
初春时节,一路上十分干旱,没有水草和牛马人烟,仅有零星的蒙古和畏吾尔居民的毡房土屋分布。陈诚看到,作为东疆重镇和交通要道,哈密国的主城地小人稠,蒙古人、穆斯林回回和依旧信奉佛教的畏吾儿杂处。当地人性格凶悍好掠,凡是过路人都会被征税。
明朝人自己绘制的《丝路山水图》
哈密位于吐鲁番以东 而不是更远的哈萨克地区
当时的哈密城较小,位于四面山地环抱的平原中央,仅在东北两面开了城门。城市中只有数百户居民,住在比较矮的土砌房屋中。城市东南有溪水,还有2-3处杏树林。本地人主食大麦,小麦和豌豆,耕田则靠收集粪便作为肥料。在向哈密统治者说明了来意后,使团还展示了国书,很快就继续踏上旅途。陈诚很留意各地的民风民俗,发现从此向西吐鲁番和火州等地的畏吾儿方言都能相通。
在鲁陈城(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市鄯善县鲁克沁镇),陈诚注意到当时各民族的服装和发型。有男性剃发,头戴小罩帽的回回男子,和以白布裹头的回回女性。还有将头发札成椎髻的畏吾儿男子,以及戴着黑色头巾,将发髻垂在额头上(垂髻于额)的畏吾儿妇女。
清朝画作中的哈密回回
当时,鲁克沁的农庄中种满葡萄,桃,杏,花红,葫芦,胡桃,小枣,甜瓜之类作物。而且陈诚还特地提到“锁子葡萄”:这种水果“甘甜而无核”,味道甘美。基于当地出产的优质葡萄,这里也有醉人的葡萄酒。除绿洲农业外,当地人还蓄养了牛羊,用骆驼和马作为交通工具。
从鲁陈城继续向西走,他们能经过一些古代的城市或寺庙遗址。随后来到火州和吐鲁番城。前者就是汉唐时期的高昌首都,和更早的汉代戍己校尉的驻地。陈诚看到高昌城远处的火焰山山壁“青红如火焰”,山壁青红,山体上的青红色色彩,仿佛是热气将山体烧得通红。鬼斧神工的丹霞地理奇观令明朝使臣们惊讶赞叹。虽然城市规模看得出这里曾经人烟稠密、佛寺密集,但现在已经非常凋敝,佛寺已经关闭过半。
哈密地区的风景 属于典型沙漠绿洲气候
这里位于亚洲内陆,而且是东天山地区。因为天山对来自大西洋水汽的阻挡,导致这里远比为位于天山迎风口的伊犁河谷地区干旱,所以陈诚笔下的哈密就是典型的沙漠绿洲环境。
相比之下,哈萨克斯坦的大部分区域根本就没有如此干旱的地表景观,更没有如此丰富的古代城邦遗址和佛教遗迹。
哈萨克斯坦境内的七河地区 远比哈密湿润
如果连永乐年间的陈诚所言都不可信,那生活在2025年的当代造谣者就更不可信!
当时草原生活风貌,参考陈诚记载,就是典型的游牧生活。由于没一点定居痕迹,很难想象明朝能在这里建立稳定的指挥使卫所:
乾坤浩荡渺无垠,雨露沾濡及远人。
喜见牛马成部落,始知蜂蚁有君臣。
酒倾酥酪银瓶冷,座拥氍毹锦帐春。
礼度不同风土异,滔滔总是葛天民。
币帛恩颁列玉盘,单于喜气溢眉端。
马嘶金勒当门立,人拥毡裘隔幔看。
握手相亲施揖让,低头重译问平安。
殷勤且慰皇华使,雪满阴山六月寒。
《至别失八里国主马哈木帐房》
明粉实际上经常质疑明朝人的见闻与结论
其实,这则谣言之所以会如此猖獗,不仅仅是因为有无法证伪的月经式造谣逻辑,还在于当代AI的以假乱真加持。两种因素叠加,制造出一堆有鼻子有眼的文言文垃圾:
从图片溯源的角度看,引用的铜印的图片的形制和包浆程度不像明代产物,年代可能比15世纪更早:
原作者为更好的混淆视听,居然用后人描述唐代西域诸国情形的古地图,告诉不明事实的人,这是明朝在西域和西亚设置了卫所的证据。
然而,无论昭武九姓,还是波斯、大食等称谓,都不是明朝人的习惯称呼。最起码到陈诚的时代,当地语言早已突厥化:
比如主要是养夷(养吉肯特),赛兰,达湿干(塔什干)、卜花儿(布哈拉)、渴石(沙赫里萨布兹)。
相比之下,后人描述唐代西域的古地图,居然还有唐人用来解释这一区域是汉代大夏字样。只能说明造谣者过于无耻,而且不学无术、水平极其低劣!
此外,北宋初年就灭亡的于阗国,也被作者强行复生。而且连位置都要调换,安置到帕米尔高原西部。显然,这是因为不知道大量于阗文物就是出土于今天的和田市周围区域。
而且和田这个名字就是来自于Khotan,这个古老的斯基泰王国名字。从2000多年前道今天,不同时代的汉字翻译都能对应到稳定称呼。不知道作者是哪里来的勇气,要将中外学术权威的历史定论彻底推翻。
最后,作者为论证自己的地图开疆扩,非要把不同时空的地理名词叠加到一起。需知,这世界上还有一本汉文与回鹘文对照的《高昌馆课》,属于明朝四夷馆下属的高昌馆编纂。其中的和田汉文写法是“兀端”,大致就是khotan的发音标注。
因此,所谓“哈萨克斯坦出土哈密卫指挥使官印”,不过是典型的历史类网络谣言。得益于AI技术的飞速发展,让无耻之徒能在只掌握只言片语的情况下,编制出臭不可闻的长篇大论。奈何底子过于拙劣,没法撑起脑中的宏大世界观配资在线导航官网,最终业绩不过止增笑耳......
发布于:上海市熊猫配资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